从口号到行动的距离有多远?
发布时间:2008-07-22 00:00浏览次数:
6
最近又到了夏收夏种的季节,农田里那些高高的麦茬以及堆积如山的麦秸秆,对农民来说最简单、最低成本的处理方式就是付之一炬、就地焚烧。季节性大气污染年复一年地困扰着人们。
去年和前年的此时,京城都遭遇了燃烧麦秸导致的外来浓烟“夜呛”,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而今夏以来,北京尚未遭遇烧秸秆造成的浓烟污染。这得益于在北京奥运的大前提下,中国的各省市都有了全国一盘棋的概念,确保北京在麦收季节“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缕烟”。
秸秆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涉及到跨省协调问题,而对于东南亚一些国家来说,已经牵涉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新加坡、马来西亚一直为邻国印尼燃烧芭叶而引起的烟雾问题无法彻底解决而苦恼。环境问题无国界,在小小的秸秆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能对环境保护起到多大的作用?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想过的问题。其结论可能是,环保事业应该是全民的、政府的,个人的力量和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我们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非常有环境意识,但行动却是偶尔为之,没有长性。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江苏或者山东的农民在以最省事的办法处理堆积如山的麦秸秆的时候,不会将这把火与北京奥运的空气质量联系起来;一个环保宣传大使,一边向大众传播“环境保护、人人有责”,一边却身着昂贵的皮草招摇过市;一些企业、机关往往选择在冷气强劲、灯火辉煌的五星级酒店举行会议,却浑然忘记了节约能源从身边做起的重要意义。
集中行政资源、严厉法规护驾,在短期内能保证秸秆禁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效,但我们要考虑的则是如何借助今年禁令的东风,在未来常态下实现效果的延续。这就需要我们研究,如何让一系列环保规定转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从口头的环保承诺落实为真正的环保行为。
也许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武进区是传统的纺织之乡、化工基地,又地处太湖上游,大量河水从这里直排入湖,环保任务很重。为了从源头上加强环保工作,武进区要求排污企业必须与具有资质的治污企业签订污染委托处理合同,企业有权自主选择具有资质的治污企业,环保部门对企业的排污状况进行测算核定,确定委托治污的年包干费用,并监督污染排放企业切实将治污费支付给签订合同的治污企业。这些治污企业由专业团队管理,实行社会化运作和规模化治污,因而摊薄了平均成本。污染排放企业在付费后,不仅把治污责任转移出去,也降低了治污成本,企业真正由过去的“偷着排”变成了现在的“不想排”、“不用排”。如武进康普药业过去自己治污时,每年的费用要100万元左右,实行委托治污后,其费用一下子降到了30多万元,并且全部达标排放。环保部门的这一以服务企业为重心的管理措施,既为企业提供了便利,又减轻了企业的治污负担,这样又省事、又省钱的治污方式,企业何乐而不为呢?
同样,对于秸秆问题,我们也应分析其难以解决的内在原因。秸秆过去是劣质燃料,现在被煤或电力取代;过去被当成肥料,现在却被化肥取代;过去用作耕牛的饲料,现在耕牛也被现代农业机械取代……秸秆逐步从传统的农业原料演变成一种无用的负担物,被排除于农业生产的内部循环之外。秸秆大量直接还田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制造秸秆蛋白饲料的生产技术尚未过关,对于农民来讲,处理也费时费力,影响农时。其他如沼气发酵和秸秆气化等一些秸秆利用技术仍不成熟,生产效率较低、经济效益差、投入产出不合算。如此看来,屡禁不止的焚烧秸秆问题,单纯依靠法规来禁止,或者依靠简单的工业化技术来转化,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想彻底解决秸秆焚烧问题,还需切实为农民提供一些符合经济效益、又有益于环境保护的秸秆处理方式。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不需要牺牲自己的任何利益,就能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近年来,一种被称为“乐活”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迅速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进而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这样的一群人倡导环保的生活方式,往往是从最小的事情做起,环保行为的成本极低,因而更容易做到。环保从口号到行动并不遥远,只要我们转换思想,改弦易辙,创造一个循环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体系,就能从中找到既符合公共利益、又有益自身的生活生产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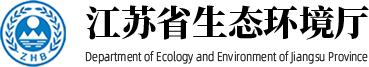
 政务微博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政务微信


 环保邮箱入口
环保邮箱入口 联系我们
联系我们 无障碍访问
无障碍访问
 机构概况
机构概况 新闻中心
新闻中心 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 生态环境质量
生态环境质量 政务服务入口
政务服务入口 互动交流
互动交流 机关党建
机关党建
 苏公网安备
苏公网安备